程章灿谈石刻是物质文化!!!
本文素材来自网络。若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违规,请联系我们删除。

程章灿(章静画)
陈寅恪说:“自古以来,学者善于金石,必是深究经史的人。不通经,就无法解读金文,没有它,就无法解读金文。”石刻是不可能通过研究历史来验证的,经书和史集是古代史料最多的地方,集子、碑文、铭文、石刻都是个别的片段,没有人不知道的。 .理解大部分收集到的数据,并能正确解释各个孤立的片段。”石刻作为“一些孤立的碎片”,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文献和历史中。研究始终处于确认和补充历史的地位,研究视角和方法也相对固定。
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程章灿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金石碑文的研究。这些出版物有《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古刻新诠》(中华书局,2009)、❄光(2009)等专着。
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将程章灿·教授的新书《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之一《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出版。它从物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石刻,呈现出与以往石刻研究截然不同的面貌。 《上海书评》邀请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苏畅谈程章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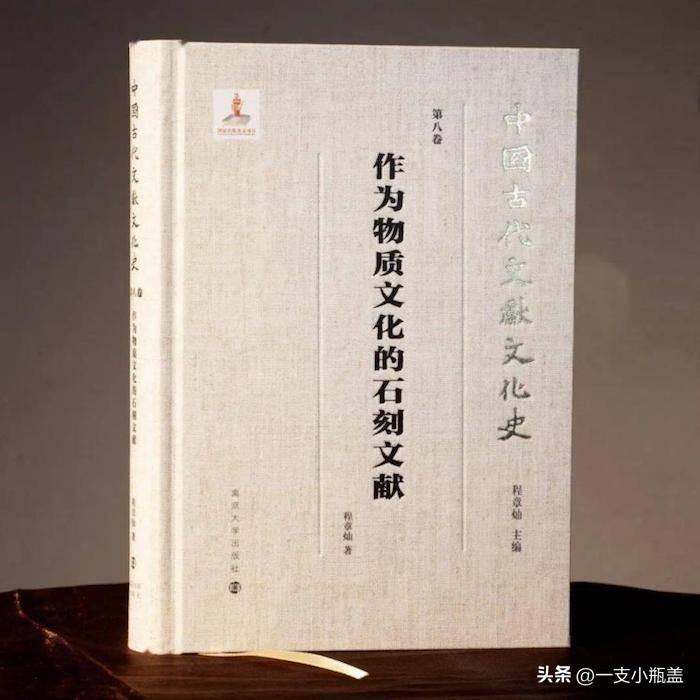
《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章灿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492页,150.00元
您的书与其他石雕专着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强调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石雕。您能谈谈选择这个视角的原因吗?
程章灿: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工作后,我把大部分学术精力投入到石刻研究上。截至2010年底,我们已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献史与文化”20余年。我以前对石雕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所说的史料研究。这是一篇通过对比石刻记载和文物文献来分析史料的考证文章。许多传统石雕研究都是如此。第二个层次是历史研究,需要汇集多个石刻文献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例如,在雕刻石雕时,我们处理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雕刻,而是涉及雕刻的所有信息。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历史研究。我之前发表的关于石刻研究的著作《古刻新诠》偏向于史料研究和《石刻刻工研究》的历史研究。

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

程章灿《古刻新诠》
我们团队在接到《中国古代文献史与文化》项目后,设计了整个项目的框架。这十卷之中,有一卷石字是我专门设计并携带的。我尝试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石刻文献这个话题进行新的探讨,最终定格在物质文化的角度。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观点,我认为这更多地与我对文档文化历史整体的思考有关,而不是仅仅关注文档的内容。所谓文件内容,是指以往我们在阅读、讨论、研究文件时,只关注其文字内容。至于文件的形式,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介质,它是如何产生和产生的,以及它的整个传播过程,过去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我们团队一起讨论的时候,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要注重文件的形式,包括材料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容易将石刻视为物质文化的产物。之前我正好对雕刻师做过一些研究。雕刻师是在石雕制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群人。这群人在石刻记录的制作乃至流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就是我想考虑的。问题。在确定了物质文化的大方向后,我尝试从各个具体角度进行展开,基本形成了本书目前的框架。 2013年前后,我院古典文学研究所举办了文字学暑期学校,主要面向国内硕士、博士生和部分青年教师。持续了两周。期间,我讲授了这本书的第一章《中国》。基本上,这个讲座涵盖了“美”的主要思想。第一章之后的十五章,大体在其范围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较为具体的研究。所谓“物质文化”的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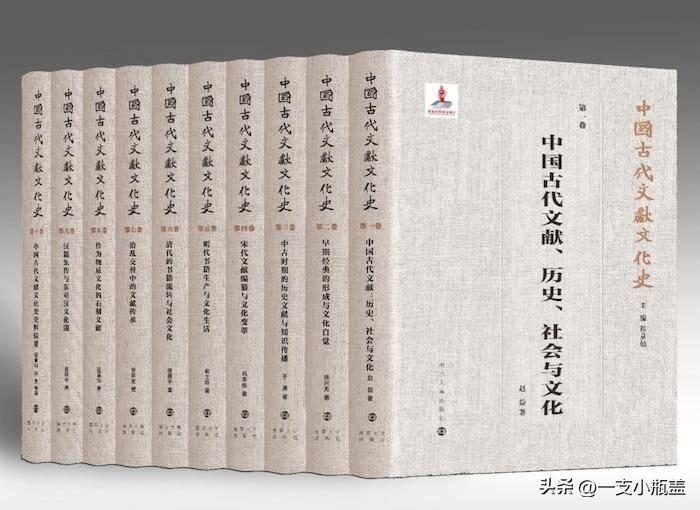
程章灿主编的系列丛书
本书第一章引出孟越、罗刚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一书。当我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思考时,我更认真地读了这本书,看看西方学者主义是如何理解物质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一个人的自我是他可以称之为自己的一切的总和。它还谈到了西方的物质文化。你所拥有的所谓财产或物质的东西,实际上是你自己的延伸。对他们来说,人几乎就像物,物也像人。
然而,传统的中国金石学研究恐怕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宋代早期学者欧阳修、赵明诚等在收集金石拓片时,对这些文物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金石录》和《后序》,我看到李清照如何使用“美丽的东西”这个词。我当时很感动,就是这个词对我很有启发。其实,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其他金石学家,有时他们并不用“美物”这个词,但所表达的感情却是相似的。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后来的金石学家使用诗歌,尤其是四行诗的形式来撰写他们的诗集和古代标题。
我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西方物质文化的书籍,但“美丽的东西”这个词对我的影响并不大。这给了我很多思考。我觉得金石本身就很有诗意,与人类的生活和很多人的感知存在息息相关。我曾经想过写一章来讨论这些可以从阅读角度写的金石摩擦诗,但实在没有时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大纲,等我感觉好点了再写。
换句话说,物质文化视角虽然强调物质,但它与物体的研究并不相同。它从物开始,最终的归宿仍然是人,以及物质、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吗?
程章灿:如果我们把石雕视为一种物质文化,对我来说,我们会考虑到人和社会的更多方面。这在书中的“礼物:汉古迹和社交网络”一章中显而易见。几年前,我一边教学生,一边读汉碑。我当时很困惑。石碑背面的铭文有什么用呢?发现物质文化的视角后,我很高兴,觉得我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它了。比如严云翔的书《礼物的流动》,是一本在农村结婚、结婚时经常使用的人际关系书。汉碑背面的题名,就像这本人伦书一样。当然,礼物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方面。
最近,《文艺研究》的编辑想让我组织一次关于文学和文化史的笔谈。我只是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所谓文献文化史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人与物的关系或者人与文献的关系。徐艳平老师最近表示,要通过问题的关联性、研究方法的融合来激发更多的问题。我觉得物与人、物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他讲的话题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思路适用于集合《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也适用于处理一定时期、一定类型的文献;也可以用来处理某个文件或者某个石雕。以我最近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为例。清朝时期,住着一位藏书家林清。他为自己制作了一部编年史,名为《鸿雪因缘图记》。他挑选了240个自己生活经历的片段,请身边的画家画出来,形成了240幅图画。每张照片都附有一段文字,介绍他出生时的样子以及后来如何当官。 ,去了很多地方,在北京买了一个花园,建了一家书店等等。这本书无疑是一份独特而独特的文献,那么您如何进行研究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文献和社会的联系,也就是因果关系。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大家都知道苏东坡的诗“人生处处知同,应如飞龙踏雪泥”。雪泥和爪子是因果。文件与外界有不同的原因和条件,即不同的文化联系。
我自己的书是对与石雕相关的各种原因和条件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更加注重石雕的文化利用。比如有一章讲朱熹,我专门讨论他对金石,特别是石雕的文化运用和改造。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了石雕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性。
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刻石文学的“四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过程语言学”的思想?
程章灿:多年来我的大部分想法都与流程有关。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走进古典的过程》,这是我四十年论文的自选集。我对这个标题非常满意。所谓“过程”,首先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成长过程;二是指文档生成的过程;三是文本创作的过程,即作品的标题、韵律、章句的形式结构以及意义生成的过程;第四是概念的形成过程,即词汇、术语、图像等形成和定型的过程。我也用英语作文来解释所谓文献的生成过程和作品的形成过程。 。我们以《鸿雪因缘图记》为例。林清是道光年间的藏书家、满族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书是这样的,图文并茂?这种图形格式是如何创建的?你经历了什么过程?文化原因很复杂。我的观点是,写书的过程涉及很多文化因素,石刻也是如此。比如说,为什么有人会在石刻上题字或者墓志铭呢?有时我们可以找到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确认坟墓主人或坟墓主人的家人与墓志铭的作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要么有亲戚关系,要么同年考进科举。比如,我们今天看一本书,发现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人的前言。为什么这个人要向这个人要这本书的前言?当然,还有很多学术和人为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从工艺角度来解释与石雕制作过程相关的各种因素。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石雕作为物质文化的意义。我认为这可以说是过程语言学的一种思想。
研究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多年来,许多书籍手稿已被复制。例如,与石刻研究密切相关的《叶长池《语石》就是一份影印手稿。打印稿件有什么意义?我们曾经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已经有了最终版本,那为什么还要打印手稿呢?现在想法不同了。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最终的想法,还需要知道你最初被放弃的想法。手稿有助于以更加立体、生动的方式回到叶长迟学术思考的现场。这就是过程的重要性。
石刻由“一”变为“四”后,带出了各种人类活动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些人物中,你似乎特别关注雕刻师和雕刻师。与石雕的作者和接受者相比,雕刻师和雕刻师是经常被忽视的小人物。您是如何关注这些人的?
程章灿:雕刻师和雕刻师的社会水平比写文章的人低,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作者经常有名人,即使没有名人,他仍然有更好的教育经历。雕刻工和门环工确实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群体。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在我们的传统记录中很少被提及,很难看到他们的记录。但自汉代以来,就有一些雕刻师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钢铁上,或许是为了“五乐公名”,或许是其他原因。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些带有工匠名字的汉代灯。但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它们是通过随机因素来区分的。汉、魏、六朝石刻中的雕刻者姓名基本上是随机出现的。我还找到了几个北魏时期的例子,有些雕刻师也有明确的身份。大概是唐朝的转折点。唐代时,官方刻师较多,这使我们可以追溯文化史或制度史。总的来说,历史上能够记载的雕刻很少。
感谢北京图书馆的曾一公先生。当我刚到古典文学研究所开始研究石刻时,我发现研究所的书架上有一本他的《石刻考工录》。 1990年,我去上海出差,在福州路的一家二手书店再次看到这本书,就买了一本回来。我经常在家看书,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样的联系,石匠经常跳舞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我想与他们接触并为他们做点什么,所以我开始收集他们的信息。后来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来研究雕刻家,他们的身份,他们与文人的交往,他们的一些贡献等等。在昆山的地方志中,我找到了刻碑的唐氏三代雕刻师的墓志铭。几代人。它们非常珍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自豪的发现。我翻了一百卷《石刻史料新编》,才找到这几句墓志铭。
浙江大学的白千深和教授此前都关注过Tuong。白老师写了《吴大澂和他的拓工》,主要是在讲吴大昌,不过他已经把作业纸拿出来了。清代以前,关于庹画的史料比版画还要少。清代尤其是晚清以后,文人之间的拓片交流相当频繁,拓片的市场也比以前大得多,拓片工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明代也有个人题词,如赵侃等。他出巡古时,带着他的学者,但记载太稀疏,难以研究。清朝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苗荃孙。他所到之处,都被陀的一些手下包围着。他时刻有意识地收集文献,拓的工人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如果说苗荃孙有一个石刻研究小组,我想这些先驱者就应该包括在内。李云从是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徐建新教授对其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后来我重新翻阅资料,发现除了苗荃孙的日记外,刘娥的日记中也经常出现李云从的身影。李云从非常重要。我觉得北京的地方志里应该有他的信息,但是我对这方面不太熟悉。也许他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贡献。
虽然我一直强调研究数据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在曾一公先生的书出版之前,清代金石学家注重篆刻,初编时只有几百人。曾一公先生起草了1000多人。我做的时候大概有4000人,现在已经2000多人了。我认为有些材料必须非常缓慢地收集。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开始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小的网络。当我们慢慢地编织它时,网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水里,我们就能捉到鱼,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天上,我们就能捉到鸟。历史意义来自于材料的不断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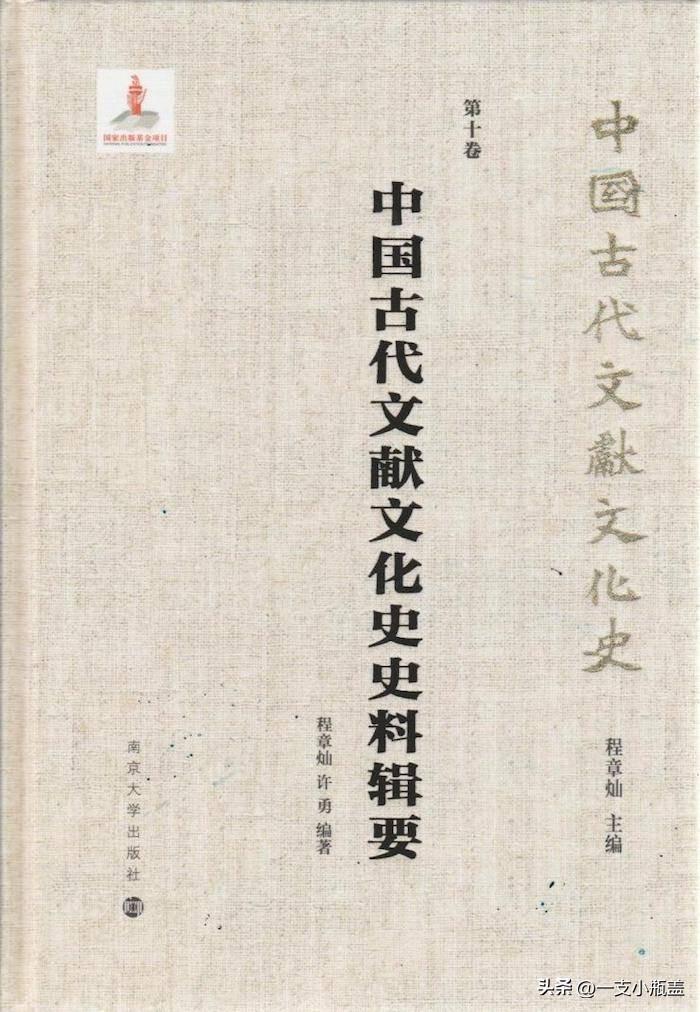
程章灿、徐勇编译《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
东西方文明的铭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与政治历史密切相关。关于标签参与政治生活,历来最受关注的是文字的书写方式。然而,你的书是关于仪式、礼物和风景的。它似乎从更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你可以谈谈。这些新观点?
程章灿:其实,我在写这些章节的时候,刻意回避了政治史的视角,因为我觉得这方面讲得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政治史的视角有它的意义,不用我再说了。如果一个物体放在那里,对我来说可以采用政治史的视角,也可以采用其他的视角,包括社会史,我更喜欢后者。基于物质文化的总体思路,我们尝试从中拓展出几个观察角度,比如风景、礼物等。我一直觉得研究社会史更有趣,解释得更清楚。因为政治史的研究往往涉及到高层的人事关系,可能无法理解。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深入社会中层甚至基层,做一些文化讨论可能更合适。
写到《礼物:汉碑与社会网络》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只有汉碑这样的材料才能让人从礼物的角度来看待石刻吗?其他类型的石雕不都是礼物吗?其他石雕师是否可以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方法可能不同。从过程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许多石雕的生产和流通都涉及社会互动,我们当然能够找到这样的材料。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和教授上了一堂阅读课,探索唐代长安城的广场。他们借助传世文献、考古报告等资料,查明了长安城的所有广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研究白居易住在哪个村子,王维住在哪个村子,元稹住在哪个村子,某个时期村里住着哪些人,他们一起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生动、三维的社会互动。如果我们采用类似的社会交往视角,我们可能会对某些石雕或者某些石雕之间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一视角可以推广到其他研究对象。
写《鸡骨剑》时,碑学与书学的结合是否有审美意义?石刻文字充当底纹图案,补充了传统的纸上书写风格或局部风格。
程章灿:我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收集古文笔记的章节出版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这一现象。上海图书馆的梁英老师写了一本叫《说笺》的书,是最好的论文研究书。梁英先生还注意到,纸的背景上有石刻,但没有展开。当我做石雕时,我对这种纸很感兴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容闳所用的古笔记集。后来在岳麓书店工作的学生回来了,把它送给了我《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这两套书确实不错。本章中的大部分材料都来自两套书。我认为你的猜测是正确的。我见过很多用碑记作为底纹的纸底纹。它确实具有钢铁和邮件融合的颜色。一方面有金石的气息,另一方面又有古雅的气息。这是他们自觉的审美追求。这与晚清碑学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有趣的是,碑学研究的发展也与铁研究“混合”在一起。
你谈到了石刻作为阅读对象的问题,我正在思考阅读墓志铭的问题。它既面对生者,又面对死者,既面对人间,又面对阴间。墓志铭的书写是否有一个先面对地下,再逐渐面对生者的时间发展过程?将墓志铭复制纳入选集后,为陌生人写墓志铭的意识是否有所提高?
程章灿:当然,墓志铭与其他类型的石雕有很大不同。大多数其他石雕都有非常明确的展示意义;墓志铭将在展示后关闭。但我认为,很难说清楚墓志铭最初是为哪些读者准备的,以及后来又是为哪些读者准备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既适用于死者,也适用于生者,现代葬礼也是如此。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具体场景来考虑。比如,在葬礼上第一次读到这篇墓志铭,与几年后在选集、展览空间或其他场合读到它的感觉完全不同。文字内容虽然相同,但时间、空间、媒介都发生了变化。考虑到这些因素,讨论墓志铭文本的解读可能会更有趣。
读完这本书后,您对下一步的石刻和文学文化史研究有新的计划吗?可以剧透一下吗?
程章灿:当然有计划,但它们是动态的并且可能会发生变化。我在7月份做这个系列丛书的发布会时,就说过我想做一本书,在江苏选择13个石碑——江苏13个地级市——每个城市选择一个石碑来代表。 。我还给这个计划起了一个名字,也许是“纪念碑”或者“铭文”。后来我想,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江苏呢?它太本地化了。从整个中国来看,视野更广阔,自由度也很大。你可以讲政治史,可以讲社会史,可以讲艺术史,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核心就是文化传承。让大家明白,中国文化不仅是通过书籍传承的,更是通过石刻传承的。
接下来我还会写一些关于石雕研究的论文。用徐艳平老师的话说,这叫“整合研究方法,激发更多问题”。我们团队是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炫耀”,但团队里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当然,我们需要互相学习,实现研究方法的融合。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献文化史?我们怎么写呢?说实话,虽然我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的项目经理,但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我认为我们集体项目最成功的一点是它“无领导”。每卷的作者都有自己特定的方法。现在项目即将结束,我发现我们的许多方法可以结合起来。我也打算从其他老师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石刻记录。当然,我也可以将石雕研究中获得的经验和方法介绍到其他相关领域。
我也准备评论2008年出版的《石刻刻工研究》。这将需要较长的时间,预计量可以在最初的基础上增加70-80%。第一版有四千多刻师,现在再增加两三千应该没有问题。我热衷于收集材料。收集雕刻师的名字,我很高兴见到一位。比4000多个名字我会高兴4000多倍。而且现在收集材料比以前方便多了。我们这一代老师只懂得使用地图或活页书。但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人的名字时,我可以用电脑查一下,看看是否添加了。它的效率要高得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及信息来源于互联网。本文作者无意针对或暗示任何实际国家、政治制度、组织、种族或个人。相应的数据和理论研究均基于网上资料。上述内容并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同意文中所述的法律、规则、观点和行为并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本文作者对上述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问题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法律责任。若文章内容包含作品内容、版权图片、侵权、八卦或其他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最后,如果你对本次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